作者:劉正要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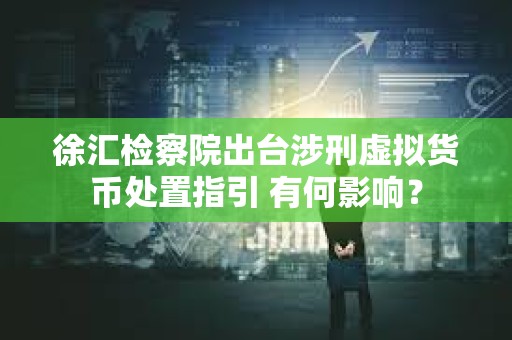
根據上海市徐匯區檢察院官方公眾號的文章,2024年8月29日徐匯區檢察院和徐匯區公安局聯合簽署了《涉刑事訴訟虛擬幣處置規范指引》(以下稱《指引》),為轄區內公、檢機關對涉虛擬貨幣刑事案件的辦理提供具體指南,具體包括“查詢固證、扣押保管、移送處置等全過程、各環節進行了更為細致、明確的規定”,詳見《網絡檢察綜合履職又一創新舉措!“光啟X空間”正式啟動》,劉律看了網上的一些分析文章,有標題黨直呼“中國首部加密貨幣犯罪處理規范出臺!”也有作者認為《指引》意在規定虛擬貨幣司法處置的具體情形。
其實這些解讀都不完全正確,鑒于“近水樓臺先得月”的便利條件,劉律師了解到《指引》的大概內容,并在本文做一個簡要分析和評論。
其實徐匯檢察院的那篇文章也講的很明白了,主題是徐匯檢察院的網絡檢察綜合履職品牌“光啟X空間”揭牌成立,該部門的主要作用就是打擊懲治新型首例網絡技術犯罪。涉虛擬貨幣犯罪作為新型網絡技術犯罪的一種,也被提到了。具體的方式就是徐匯區的公檢兩家簽署的《指引》。
該《指引》內容并不算多,主要就是涉及到虛擬貨幣類刑事案件中對于涉幣類的證據(電子證據為主)如何合法合規地進行查詢、固定;涉案虛擬貨幣(同時兼具證據屬性和財產屬性)如何進行扣押和保管;以及涉案虛擬貨幣的移送和處置的概括性要求等內容。
坦白來講《指引》并不會對整個幣圈的刑事辯護產生多么大的影響。主要還是因為這個《指引》僅僅是徐匯區的一個辦案規范性文件,對隔壁區都沒啥直接的影響力,何談對上海市乃至全國的影響了。
除了地域性的限制以外,《指引》也并非一些文章所謂的“中國首部加密貨幣犯罪處理規范”,僅劉律師知道并確實拿到相似的各種涉幣類刑事案件辦理規范或指引原文的至少已經有5個了,有些是公安省廳級的,有些是市局級的。如果說區縣級的處置規范,上海徐匯確實應該是第一個。
總體上來說,已有的規定中各地都大同小異。有關網絡犯罪中的證據標準、取證程序等內容“兩高一部”早已做了明確的規定(比如2022年的《關于辦理信息網絡犯罪案件適用刑事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2021年最高檢的《人民檢察院辦理網絡犯罪案件規定》),幣圈的刑事案件全都可以涵蓋在網絡犯罪的大概念之下。所以目前來說很難在全國范圍內由“兩高一部”專門再為虛擬貨幣刑事案件出臺一個什么規定,更多的會像之前的“洗錢罪司法解釋”“非法集資司法解釋”一樣,在修訂一些罪名司法解釋時,將虛擬貨幣的內容增加進去(兩個例外情形:一是幣圈的刑事案件數量足夠多,證據、法律適用有了特殊變化,比如法律中增加虛擬貨幣內容;二是對虛擬貨幣的處置出臺專門的規定)。
目前涉案虛擬貨幣處置的爭論之一就是處置時機或者說處置機關問題,根據法律或司法解釋等規定,刑事案件中涉案財物原則上都是由法院進行處置。但是虛擬貨幣刑事案件中,當下的司法實務多是由公安機關直接進行處置,劉律師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分析過,從公安機關的角度來說,其處置依據是:
1.公安機關涉案財物管理若干規定
“對于因···市場價格波動大的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和有效期即將屆滿的匯票、本票、支票等,權利人明確的,經其本人書面同意或者申請,并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主要負責人批準,可以依法變賣、拍賣,所得款項存入本單位唯一合規賬戶。”
2.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
“在偵查期間,對于易損毀、滅失、腐爛、變質而不宜長期保存,或者難以保管的物品,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主要負責人批準,可以在拍照或者錄音錄像后委托有關部門變賣、拍賣,變賣、拍賣的價款暫予保存,待訴訟終結后一并處理。”
“對凍結的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應當告知當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有權申請出售。”
甚至對于檢察院來說,在滿足一定條件時,也可以在辦案過程中處置涉案財產。
3.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
“凍結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應當書面告知當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有權申請出售。”
具體的處置為當事人申請、檢察長批準后,可以在未結案前對涉案的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進行出售或變現,所得價款轉入檢察院的銀行專戶。
虛擬貨幣基于其匿名性、去中心化等特征相較于傳統財物的保管有較大不同,嫌疑人/被告人的虛擬貨幣被扣押后又丟失的案例不止一次發生過。原因就在于辦案機關沒有及時將涉案虛擬貨幣轉移進入新的錢包地址,一旦除嫌疑人/被告人以外的人也掌握錢包私鑰(助記詞)的話,很容易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涉案虛擬貨幣的轉移;
此外,虛擬貨幣的市場波動極大,幣價可以在一天之內過山車式地上漲或下跌,如果最終變現時所得價款遠遠高于/低于案發時價款,那么無論是對于公訴機關或是對于辯護人,都是難以接受的(因為當事人最終的量刑可能極重/極輕,甚至可能無罪,比如涉案的虛擬貨幣價值歸零時該如何指控?),所以處置的越及時,未來在訴訟中訴辯對抗的力度可能會越小。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公安機關或者檢察院,甚至法院在處置涉案虛擬貨幣時面臨的問題是:
第一,虛擬貨幣并不是“匯本支”,也非“債股基”,公安也好,檢察院也罷處置虛擬貨幣都有“師出無名”之嫌;
第二,當下對于虛擬貨幣的監管文件中,不允許任何人開展虛擬貨幣和法幣的變現業務活動,公安機關為此委托第三方處置公司進行涉案虛擬貨幣的處置業務,此模式與當下的監管規定是否吻合仍有爭議;
第三,總體上來說,當下涉案虛擬貨幣處置并無明確的、統一的規范或指引可以參考,導致實務中各地辦案機關“自說自話”“摸不同的石頭過河”,形成了不同的基層經驗。其中《指引》就算是其中的一種,但是劉律師認為《指引》的出臺還是有積極意義的,如果能夠公開給全體公民意義就更大了(或者徐匯轄區公民也行)。
回到本節開頭的問題,如果說《指引》對于處置虛擬貨幣有影響,也僅局限在上海市徐匯區,同時也很難逃出劉律師上面列舉的正反兩方面問題的限制。
最近有關涉案虛擬貨幣處置的消息真是應接不暇,從最高院的課題招標到人民法院報的文章(詳見本文結尾的“往期推薦”),再到上海市徐匯區的指引,這些都說明一個問題: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司法機關關注到涉案虛擬貨幣處置領域的合規問題,甚至處置合規的需求已經刻不容緩了。這也給第三方處置商提了一個警示:唯有合規,方能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