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4日的“中國檢察官”公眾號發布了一篇《疑案精解 | 涉虛擬貨幣洗錢行為的司法認定》,作者是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的兩位檢察官的文章,介紹了現在虛擬貨幣交易中非常常見、典型的場外交易被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案例,劉律師寫此小文做一簡要分析,同時也算是給正在做U商的朋友們做個風險提示。
作為U商的肖某在“電報”上認識了一個跑分集團的老板,名號“大上海”。“大上海”通過卡農將電詐資金取現后找到肖某購買USDT泰達幣,肖某通過高出交易所2分錢的價格在場外大量收購USDT,再加價5分錢賣給“大上海”。檢察官在撰文時還很細心地提出來肖某和“大上海”的交易細節,比如雙方在線下交易時,肖某在現場對現金進行清點后,會先轉價值100元的USDT到“大上海”的錢包地址,待“大上海”確認收到USDT保證交易渠道通暢安全時,肖某再將剩余USDT轉入。截至案發,肖某獲利共計6000余元,最終被法院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3年3個月的有期徒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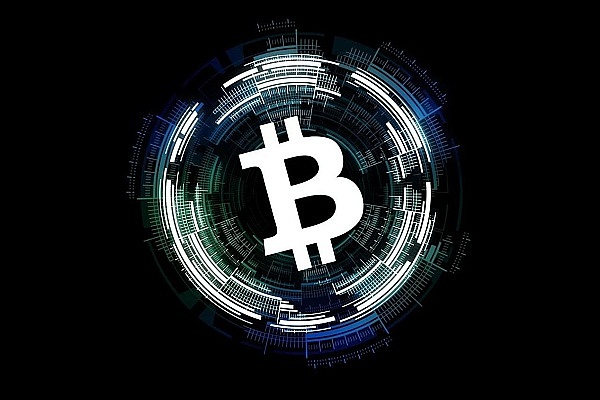
肖某的行為屬于典型的U商賺差價,但沒有做KYC最終導致被抓的案例。雖然獲利才6千元(似乎這個金額在幣圈實在是不好意思拿出來說),但是失去3年3個月的自由可是實打實的。
圍繞肖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有兩種不同意見,即無罪和有罪:
無罪派認為:肖某主觀上并不知道“大上海”拿出來的現金是贓款,不知者無罪;此外,肖某是用虛擬貨幣和“大上海”交易的,而虛擬貨幣能否作為犯罪工具或犯罪對象,目前國內還有爭議。
有罪派主張:肖某明顯構成洗錢類犯罪,具體應該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肖某的行為具有逃避偵查的明顯意圖,如使用加密軟件通信,交易價格高于市場價,交易的頻率較為固定、場所較為隱蔽等,可以推斷他明知“大上海”的錢來路不正;此外,虛擬貨幣具有經濟價值,屬于刑法上的犯罪對象或犯罪工具。

本案中肖某構成的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這個罪需要滿足“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所以對于廣大的U商朋友,你在每一筆交易時,是否明知交易對象涉及的資金是否是犯罪所得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司法機關對于當事人是否明知,至少有兩種方式去考察:一是直接訊問,有合法合規的訊問,也有誘供、騙供等非法方式的訊問,只要被訊問人承認了其明知交易對手的資金是犯罪所得,那么在當下的司法實務中基本上就“坐實了”當事人明知的主觀因素。至于說對于當事人被誘供、騙供等作出的筆錄能不能被排除,要看當事人能否拿出證據來證據自己被誘供和騙供了;二是推定明知,也就是即使當事人自己不承認明知,無論公安怎么訊問,當事人都是頭鐵如鋼,那么司法機關也會從其他方面來驗證當事人是否為明知,比如:
(一)沒有正當理由,通過非法途徑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
(二)沒有正當理由,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收購財物的;
(三)沒有正當理由,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于市場的“手續費”的;
(四)沒有正當理由,協助他人將巨額現金散存于多個銀行賬戶或者在不同銀行賬戶之間頻繁劃轉的;
(五)協助近親屬或者其他關系密切的人轉換或者轉移與其職業或者財產狀況明顯不符的財物等。
當事人一旦被司法機關推定為明知交易對手的資金為犯罪所得而仍與之交易,那么當事人就與幫信罪、掩隱罪、洗錢罪等犯罪不遠了。在長寧檢察院看來,肖某作為虛擬貨幣交易老手,通過“電報”認識的“大上海”與其缺乏信任基礎,仍然“故意繞開較為成熟的虛擬貨幣交易場所,采取隱蔽軟件聯系、隱蔽地點接頭的方式收取對方錢款,后將所收到的錢款以虛擬貨幣的形式打入對方賬戶”并收取高于市場的手續費等行為屬性明顯的幫助對方洗錢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

如今U商的日子算是越來越難過了,本來就是灰色市場,隨著市場競爭愈發激烈,本來利潤空間就不斷被壓縮;現在司法機關又開始緊盯著U商們的一舉一動,稍有不慎就“大刑伺候”。未來的路到底是“荊棘盡頭是坦途”還是“陡崖峭壁無盡頭”,劉律師也不好說,但是對于廣大U商們來說,對于當下腳下的路修修補補似乎還是可以再堅持一段時間的,至于如何修補?那就是參考肖某,反其道而行之:使用國內通訊軟件、手續費不要明顯高于交易所、做好交易對手的KYC等,實在拿不準就咨詢劉律師吧。